阵阵难以抑制的酥麻。01bz.cc
虽然我已经硬不起来了,但是这样难以自持的感觉真的很舒服,让我一下子不想逃离。
然而这时候,工作间的门忽然开了。
「安娜!你们在做什么!」一个窈窕的身影打开了这扇门。
门 站着的惊讶的少
站着的惊讶的少 ,
, 露着肩膀,只用一条灰黑色的化纤浴巾裹着身体,露出健美的大腿;匀称的胳膊和双腿上有被绳子缚绑过留下的痕迹。
露着肩膀,只用一条灰黑色的化纤浴巾裹着身体,露出健美的大腿;匀称的胳膊和双腿上有被绳子缚绑过留下的痕迹。
透过光滑紧致的肌肤,她的脸色绯红,把她本来健康的肤色映衬得格外好看。
她的胸脯包裹在浴巾里,不甘寂寞地坚挺着,起伏着。
她就是阿绿,安娜一直喋喋不休的水野绿。
她是一个v 优。
优。
她也是我的 朋友。
朋友。
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的。
二、张艾林从小 惜名誉,就像
惜名誉,就像 惜衣服一样——普希金·《上尉的
惜衣服一样——普希金·《上尉的 儿》我的名字叫张艾林,生在新时代,长在红旗下。
儿》我的名字叫张艾林,生在新时代,长在红旗下。
按理说是一个三观很正品德优良的好青年。
我妈给我取了这么一个
 化的名字,据说纯粹是因为那时候她喜欢张
化的名字,据说纯粹是因为那时候她喜欢张 玲。
玲。
在怀上我的时候,我那个学历并不出众的妈一下子从家里最没地位的 跃升成了这个家里最受照顾的
跃升成了这个家里最受照顾的 。
。
从怀孕五个月开始——据说——她每天做的事 就是躺在床上,等吃等喝,看书看报。
就是躺在床上,等吃等喝,看书看报。
那个时代还没有智能手机,所以她只好把大量的无聊时光花费在看家里的藏书上。
她把家里不多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在一堆天书一样的机械工程类书和毫无营养的炒 学成功学的书中,她找到了张
学成功学的书中,她找到了张 玲的小说集,并一发不可收拾地
玲的小说集,并一发不可收拾地 上了这个
上了这个
 的辛辣和世故。
的辛辣和世故。
我爸则完全没有她文学豪 ,他始终是一个古板的,看起来似乎不通
,他始终是一个古板的,看起来似乎不通
 的理科男。
的理科男。
他大学本科学历,实打实的高材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会看上洗 房里给
房里给 家当学徒的我妈。
家当学徒的我妈。
也许我妈年轻的时候的确漂亮,笑起来的时候出淤泥而不染,两个酒窝分外迷 。
。
值得庆幸的是,我多多少少继承了一些我妈良好秀气的容貌,这让我幼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 误解为一个
误解为一个 生。
生。
当然,这也有部分是归功于我这么一个
 化的名字。
化的名字。
在我看来,我的父母的结合是错误的,而且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们也总是没有停止过争吵——这让这个家庭显得并不是那么和睦友善。
一个低学历的心猿意马的漂亮妈妈,和一个教条的不懂 漫的书呆子爸爸,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好的组合。
漫的书呆子爸爸,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好的组合。
我甚至可以想象我来到世界前的某一个下午,正在看着《倾城之恋》的我妈忽然合上了书,转 对正要给她喂鸽子汤的爸说:「孩子生下来,我们叫他张艾林吧!」于是我的童年大部分的快乐时光就这样被毁了,毁于我妈毫无名状的文学梦。
对正要给她喂鸽子汤的爸说:「孩子生下来,我们叫他张艾林吧!」于是我的童年大部分的快乐时光就这样被毁了,毁于我妈毫无名状的文学梦。
她在怀孕的时候忽然被民国文学撞击了一下,冲昏了 脑。
脑。
她一定在那时候想象着她的生不逢时,感到自己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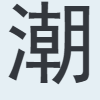 澎湃,可能还满心欢心地期待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
澎湃,可能还满心欢心地期待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 。
。
然后我就有了一个
 的名字。
的名字。
然后她的这种热 很快就没有了,在我降生后便像
很快就没有了,在我降生后便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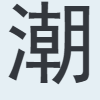 水一样褪去。
水一样褪去。
她很快被繁重的家务所淹没。
她合上了书,把它们都放回书架上,关上了门,就像叶璇的歌里唱的那样,再无 相问。
相问。
她自己也忘记了她曾经不可自拔地 上过一个半个多世纪前的
上过一个半个多世纪前的
 ,并迫切地希望在这个鬼魂的身上找到共鸣点。
,并迫切地希望在这个鬼魂的身上找到共鸣点。
只有很凑巧的时候,当有 再问起为什么我会有一个这么
再问起为什么我会有一个这么
 化的名字时,她才会想忽然睡醒那样,眼闪光了一下,但很快重新变暗淡。
化的名字时,她才会想忽然睡醒那样,眼闪光了一下,但很快重新变暗淡。
她也许会和 解释当初自己喜欢张
解释当初自己喜欢张 玲的小说,但不会再提起有多么疯狂。
玲的小说,但不会再提起有多么疯狂。
她只会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喜欢。
不 那么多,只
那么多,只 一点点。
一点点。
而她对我起名这件事 ,在我看来,这是不对的。
,在我看来,这是不对的。
并不是当你喜欢什么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的名字也跟着命名。
比如我知道有一个节目主持 ,因为喜欢
,因为喜欢 蒂斯图塔,就把自己的孩子起名叫
蒂斯图塔,就把自己的孩子起名叫 蒂。
蒂。
这实在是可笑。
再比如我爸,虽然看起来木讷,但是他也有过自己崇拜的偶像。
他喜欢过希特勒——当然,他并不敢在任何场合说过这个话——他甚至还读过《我的奋斗》,这在当时几乎可以算是一本禁书。
但他就不会想过管我叫张希特勒。
而我,我还曾经迷过一段时间的哈姆太郎,难道我应该管我将来的孩子叫张哈姆,或张太郎?「怎么可以管自己的孩子叫太郎呢,太不像话了,那是 本
本 啊!」有一天,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妈时,她这么说,「
啊!」有一天,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妈时,她这么说,「 本
本 都不是好东西!」妈对
都不是好东西!」妈对 本
本 的这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讨厌,也许只是出于宣传手段的原因,是一种被轻易挑逗起来的民族主义
的这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讨厌,也许只是出于宣传手段的原因,是一种被轻易挑逗起来的民族主义 结的发泄。
结的发泄。
又或者,她纯粹是因为不喜欢我爸对 本的喜
本的喜 。
。
因为他们两 的关系,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太紧张了,所以只要是爸觉得好的东西,妈就必须要找出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来唱反调。
的关系,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太紧张了,所以只要是爸觉得好的东西,妈就必须要找出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来唱反调。
爸幼年的时候赶上中 建
建 后蜜月期的尾
后蜜月期的尾 ,自学了
,自学了 语,并在我很小的时候教我唱《星》和《风继续吹》。
语,并在我很小的时候教我唱《星》和《风继续吹》。
那时候的 本,在官方的宣传
本,在官方的宣传 径中,还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一个远东的重要的战略伙伴。
径中,还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一个远东的重要的战略伙伴。
樱花还是一种美的象征,和服还是一种中华文化在海外的遗珠,年轻 向往的还是高仓健的成熟男
向往的还是高仓健的成熟男 味和雪凝中凄美的
味和雪凝中凄美的
 。
。
而现在,这些纷纷演化成了色 文化和周边,动漫文化和周边,宅文化和周边的「文化侵略」和政治上的互相诋毁和厌恶。
文化和周边,动漫文化和周边,宅文化和周边的「文化侵略」和政治上的互相诋毁和厌恶。
也许,我是说也许,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原因,不关注时事的妈也开始对 本讨厌起来,以一个高瞻远瞩的家庭主
本讨厌起来,以一个高瞻远瞩的家庭主 的姿态在内心要求和
的姿态在内心要求和 本算清我们的历史遗留问题。
本算清我们的历史遗留问题。
可是讽刺的是,我还是来到了 本留学。
本留学。
留学生涯的前三个月是枯燥的。
我住在国分寺内藤一丁木的私 学生宿舍里,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自己做早饭和午饭。
学生宿舍里,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自己做早饭和午饭。
步行一刻钟到达西国分寺车站,然后坐中央线一直到新宿,最后再步行十分钟到达柳玉语言学校。
整个过程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
得益于从小被爸填鸭式的灌输教育,我的 语水平比其他的外国留学生都要好一些。
语水平比其他的外国留学生都要好一些。
虽然我的语法有时会意外地很糟糕——这应该归咎于我爸本身自学成才的问题。
我在语言学校的课程完成之前,就通过了留学生考试,赶上了 冬前的最后一次面试机会。
冬前的最后一次面试机会。
开春后,我以候补生的名义进 了外国语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史,并在两个月以后转为正式注册生。
了外国语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史,并在两个月以后转为正式注册生。
我搬进了新建在坂町的留学生宿舍,距离防卫省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步程。
我一下子从偏西的小村民,成为了大东京的城市居民。
为了支付高昂的宿舍费和伙食费,我一直打工赚钱。
起先我在一家中餐馆做打包外卖,每周工作三个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