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 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
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
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
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 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
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
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苏东坡时,书籍的印刷早
已约有百年之久。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 毕升所发明。方法是把一种特
毕升所发明。方法是把一种特
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字刻好之后,胶泥变硬;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
的金属盘子上,字板按行排好之后,将胶加热,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
的字板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印书完毕之后,再将树胶加热,各字板便从金属盘
上很容易脱落下来,予以清洗,下次再用。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
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当年那种考
试,要符合某些标准,须要下过某等的苦工夫,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忆力,当然还
要一般正常的智力。智力与创造力过高时,对考中反是障碍,并非有利。好多有才
气的作家,像词 秦少游,竟而一直考不中。苏洵的失败,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
秦少游,竟而一直考不中。苏洵的失败,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
上。诗的考试,须要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措词相当的 巧工稳,而苏洵则主要重
巧工稳,而苏洵则主要重
视思想观念。因为读书 除去教书之外,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父亲名落孙
除去教书之外,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父亲名落孙
山而归,必然是懊恼颓丧的。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
生的一大乐事。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
多困难。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
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 大概正如一个猎
大概正如一个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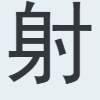
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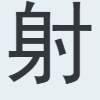 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
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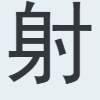 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
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
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
药而愈。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在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
而雏风清于老风声了。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苏洵天赋较高,但是为
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
虽未能考中,若因此对儿子高中还不能坚信不疑,那他才是天下一大痴呆呢。说这
话并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 研史书
研史书
为政之法,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我们并非不知。
对苏东坡万幸的是,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醇朴风格,力诫当时流行的华美靡
丽的习气;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晋京赶考之时,礼部尚书与礼部主试欧阳修,都决
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便藉着那个机会,把只耽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词藻的华美
靡丽之文的学子,全不录取。所谓华美靡丽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堆砌艰 难解之词
难解之词
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在此等文章里,很难找到一两行朴质自然的
句子。最忌讳指物直称其名,最怕句子朴质无华。苏东坡称这种炫耀浮华的文章里
构句用字各自为政,置全篇效果于不顾,如演戏开场 ,项臂各挂华丽珠宝的老姬
,项臂各挂华丽珠宝的老姬
一样。
这个家庭的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各种图书 列满架。祖
列满架。祖
父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因为次子已官居造务监裁,为父者也曾蒙思封赠为“大
理评事”。此等官爵完全是荣誉 的,主要好处是使别的官员便于称呼。有时似乎
的,主要好处是使别的官员便于称呼。有时似乎
是,求得这么一个官衔刻在墓志铭上,这一生才不白过——等于说一个 若不生而
若不生而
为士绅,至少盼望死得像个士绅。若不幸赶巧死得太早,还没来得及获得此一荣耀,
死后还有一种方便办法,可以获得身后赠予的 衔。其实在宋朝,甚至朝廷正式官
衔。其实在宋朝,甚至朝廷正式官
员,其职衔与真正职务也无多大关系。读者看苏家的墓志铭,很容易误以为苏东坡
的祖父曾任大理评事,甚至做过太傅,而且误以为他父亲也做过太子太傅——其实
这些荣耀 衔都是苏辙做门下侍郎时朝廷颁赠的。苏东坡这时有个叔父做官,两个
衔都是苏辙做门下侍郎时朝廷颁赠的。苏东坡这时有个叔父做官,两个
姑母也是嫁给做官的。因此他祖父和外祖父都拥有官衔,一个是荣誉的,另一个是
实际的,刚才已经说过。
在苏家,和东坡一齐长大一齐读书而将来也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他弟弟辙,
字子由。他们兄弟之间的友 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
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 厚的手足之
厚的手足之 ,是苏东坡这
,是苏东坡这
个诗 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
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 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
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
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甚至在中国伦理道德之邦,兄弟间似此友 之美,
之美,
也是绝不寻常的。苏子由生来的气质是恬静冷淡,稳健而实际,在官场上竟尔比兄
长得意,官位更高。虽然二 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宦海浮沉的荣枯相同,子由冷
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宦海浮沉的荣枯相同,子由冷
静而机敏,每向兄长忠言规劝,兄长颇为受益。也许他不像兄长那么倔强任 ;也
;也
许因为他不像兄长那么才气焕发,不那么名气非凡,因而在政敌眼里不那么危险可
怕。现在二 在家读书时,东坡对弟弟不但是同学,而且是良师。他写的一首诗里
在家读书时,东坡对弟弟不但是同学,而且是良师。他写的一首诗里
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子由也在兄长的墓
志铭上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走笔至此,正好说明一下三苏的名宇。根据古俗,一个中国读书 有几个名字。
有几个名字。
除去姓外,一个正式名字,在书信里签名,在官家文书上签名,都要用此名字。另
外有一个字,供友

 与文字上称呼之用。普通对一个
与文字上称呼之用。普通对一个 礼貌相称时,是称字而
礼貌相称时,是称字而
不提姓,后而缀以“先生”一词。此外,有些学者文 还另起雅号,作为书斋的名
还另起雅号,作为书斋的名
称,也常在印章上用,此等雅号一旦出名之后, 也往往以此名相称。还有
也往往以此名相称。还有 出了
出了
文集诗集,而别 也有以此书名称呼他的。另外有
也有以此书名称呼他的。另外有 身登要职,全国知名,
身登要职,全国知名, 也以
也以
他故乡之名相称的。如曾湘乡,袁项城便是。
老苏名询字明允,号老泉,老泉是因他家乡祖莹而得名。长子苏轼,字子瞻,
号东坡,这个号是自“东坡居士”而来,“东坡居士”是他谪居黄州时自己起的,
以后,以至今 ,他就以东坡为世
,他就以东坡为世 所知了。中国的史书上每以“东坡”称他而不
所知了。中国的史书上每以“东坡”称他而不
冠以姓,或称东坡先生。他的全集有时以溢法名之,而为《苏文忠公全集》,宋孝
宗在东坡去世后六十年,赠以“文忠公”溢法。文评家往往以他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