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同一本书里还讨厌燔祭和集会,却要求信奉者“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者,给孤儿伸冤,为寡 辨屈”。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也强调:“世上的,选择了最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种视天下受苦
辨屈”。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也强调:“世上的,选择了最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种视天下受苦 为自家骨
为自家骨 的
的 怀,以及相应的慈善制度,既是一种伦理,差不多也是一种政纲。这与儒家常有的圣王一体,与亚里士多德将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都甚为接近;与后来某些宗教更醉心于永恒(道教)、智慧(佛教)、成功(福音派)等等,则形成了侧重点的差别。
怀,以及相应的慈善制度,既是一种伦理,差不多也是一种政纲。这与儒家常有的圣王一体,与亚里士多德将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都甚为接近;与后来某些宗教更醉心于永恒(道教)、智慧(佛教)、成功(福音派)等等,则形成了侧重点的差别。
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也不乏西哲的同道。《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称“王者以民为天”。《左传》称“夫民,之主也”。而《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也明显含有关切民众的天道观。稍有区别的是,中国先贤们不语“怪力 ”,不大习惯
”,不大习惯 格化、传化、话化的赎救故事,因此最终没有走向学。虽然也有“不愧屋漏”或“举
格化、传化、话化的赎救故事,因此最终没有走向学。虽然也有“不愧屋漏”或“举 明”(见《诗经》等)之类玄语,但对
明”(见《诗经》等)之类玄语,但对 们
们 顶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语焉不详,或搁置不论。在这里,如果说西方的“天赋
顶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语焉不详,或搁置不论。在这里,如果说西方的“天赋 权”具有学背景,是宗教化的;中国的“奉民若天”则是玄学话语,具有半宗教、软宗教的品格。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置最广大
权”具有学背景,是宗教化的;中国的“奉民若天”则是玄学话语,具有半宗教、软宗教的品格。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置最广大 民群众的利益于道德核心,其“上帝”也好,“天道”也好,与“
民群众的利益于道德核心,其“上帝”也好,“天道”也好,与“ 民”均为一体两面,不过是道德的学符号或玄学符号,是
民”均为一体两面,不过是道德的学符号或玄学符号,是 工程的形象标识,一种方便于流传和教化的代指。
工程的形象标识,一种方便于流传和教化的代指。
想想看,在没有现代科学和教育普及的时代,他们的大众传播事业又能有什么招?
“上帝死了”,是尼采在十九世纪的判断。但上帝这一符号所聚含的 民
民 怀,在学动摇之后并未立即断流,而是进
怀,在学动摇之后并未立即断流,而是进 一种隐形的延续。如果
一种隐形的延续。如果 们注意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出自僧侣群体,然后从卢梭的“公民宗教”中体会出宗教的世俗化转向,再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听到“天国”的意味,从“无产阶级”礼赞中读到“弥赛亚”“特选子民”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蓝图,嗅出教堂里平均分配的面包香和菜汤香,嗅出土地和商社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这与毛泽东强调“为
们注意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出自僧侣群体,然后从卢梭的“公民宗教”中体会出宗教的世俗化转向,再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听到“天国”的意味,从“无产阶级”礼赞中读到“弥赛亚”“特选子民”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蓝图,嗅出教堂里平均分配的面包香和菜汤香,嗅出土地和商社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这与毛泽东强调“为 民服务”,宣称“这个上帝不是别
民服务”,宣称“这个上帝不是别 ,就是全中国的
,就是全中国的 民大众”(见《毛泽东选集》),同样具有历史
民大众”(见《毛泽东选集》),同样具有历史 ——毛及其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这一古老道统的现代传
——毛及其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这一古老道统的现代传 。
。
这样,尼采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只死了一半。换句话说,只要“ 民”未死,只要“
民”未死,只要“ 民”、“穷
民”、“穷 ”、“无产者”这些概念还闪耀圣光辉,世界上就仍有潜在的大价值和大理想,传统道德就保住了基本盘,至多是改换了一下包装,比方由一种前科学的“上帝”或“天道”,通过一系列语词转换,蜕变为后学或后玄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共产主义早期事业一直是充满道德激
”、“无产者”这些概念还闪耀圣光辉,世界上就仍有潜在的大价值和大理想,传统道德就保住了基本盘,至多是改换了一下包装,比方由一种前科学的“上帝”或“天道”,通过一系列语词转换,蜕变为后学或后玄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共产主义早期事业一直是充满道德激 、甚至是宗教感的,曾展现出一幅幅圣战的图景。团结起来投
、甚至是宗教感的,曾展现出一幅幅圣战的图景。团结起来投 “最后的斗争”,《国际歌》里的这一句相当于《圣经》stdy(最后的
“最后的斗争”,《国际歌》里的这一句相当于《圣经》stdy(最后的 子),迸放着大同世界已近在咫尺的感觉,苦难史将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很多后
子),迸放着大同世界已近在咫尺的感觉,苦难史将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很多后 难以想象的那些赴汤蹈火、舍身就义、出生
难以想象的那些赴汤蹈火、舍身就义、出生 死、同甘共苦、先
死、同甘共苦、先 后己、道不拾遗,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是一两代
后己、道不拾遗,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是一两代
 骨的亲历
骨的亲历 记忆。他们内心中燃烧的道德理想,来自几千年历史
记忆。他们内心中燃烧的道德理想,来自几千年历史 处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丰镐和洛邑,曾经一度沉寂和蓄藏,但凭借现代
处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丰镐和洛邑,曾经一度沉寂和蓄藏,但凭借现代 对理
对理 和科学的自信,居然复活为一种政治狂飙,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呼啸了百多年,大概是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和科学的自信,居然复活为一种政治狂飙,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呼啸了百多年,大概是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问题是“ 民”是否也会走下坛?或者说,
民”是否也会走下坛?或者说, 民之死是否才是上帝之死的最终完成?或者说,
民之死是否才是上帝之死的最终完成?或者说, 民之死是否才是福柯“
民之死是否才是福柯“ 之死(mnd)”一语所不曾揭
之死(mnd)”一语所不曾揭 和说透的最重要真相?冷战结束,标举“
和说透的最重要真相?冷战结束,标举“ 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挫,柏林墙后面的残
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挫,柏林墙后面的残 、虚伪、贫穷、混
、虚伪、贫穷、混 等内
等内 震惊世
震惊世 ,使十九世纪以来流行的“
,使十九世纪以来流行的“ 民”、“
民”、“ 民
民 ”、“
”、“ 民民主”一类词蒙上
民民主”一类词蒙上 影——上帝的红色代用品开始贬值。“为
影——上帝的红色代用品开始贬值。“为 民服务”变成“为
民服务”变成“为 民币服务”,是后来的一种粗俗说法。温雅的理论家们却也有权质疑“
民币服务”,是后来的一种粗俗说法。温雅的理论家们却也有权质疑“ 民”这种大词,这种整体
民”这种大词,这种整体 、本质
、本质 、圣
、圣 、政治
、政治 的概念,是否真有依据?就拿工
的概念,是否真有依据?就拿工 阶级来说,家居别墅的高级技工与出
阶级来说,家居别墅的高级技工与出 棚户的码
棚户的码 苦力是一回事?摩门教的银行金领与什叶派的山区
苦力是一回事?摩门教的银行金领与什叶派的山区 工很像同一个“阶级”?特别在革命退
工很像同一个“阶级”?特别在革命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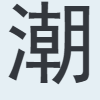 之后,当行业冲突、地区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升温,工
之后,当行业冲突、地区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升温,工 与工
与工 之间几乎可以不共戴天。一旦遇上全球化,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富得一个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穷得不一个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无国界地发财,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国界地打工;于是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工会组织,更容易为争夺饭碗而怒目相向,隔空
之间几乎可以不共戴天。一旦遇上全球化,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富得一个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穷得不一个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无国界地发财,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国界地打工;于是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工会组织,更容易为争夺饭碗而怒目相向,隔空 战,成为国际对抗的重要推手。在这种
战,成为国际对抗的重要推手。在这种 况下,你说的“
况下,你说的“ 民”、“穷
民”、“穷 ”、“无产者”到底是哪一伙或者是哪几伙?前不久,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遭遇一次尴尬:他力主向大矿业主加税,相信这种保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义举,肯定获得选民的支持。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恰好是选民通过民调结果把他哄下了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中下层
”、“无产者”到底是哪一伙或者是哪几伙?前不久,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遭遇一次尴尬:他力主向大矿业主加税,相信这种保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义举,肯定获得选民的支持。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恰好是选民通过民调结果把他哄下了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中下层 士即便不靠矿业取薪,也通过
士即便不靠矿业取薪,也通过 票等等与大矿业主发生了利益关联,或通过媒体鼓动与大矿业主发生了虚幻的利益关联,足以使工党的传统政治算式出错。
票等等与大矿业主发生了利益关联,或通过媒体鼓动与大矿业主发生了虚幻的利益关联,足以使工党的传统政治算式出错。
“ 民”正在被“
民”正在被“ 民”、“基民”、“彩民”、“纳税
民”、“基民”、“彩民”、“纳税 ”、“消费群体”、“劳力资源”、“利益关联圈”等概念取代。除了战争或灾害等特殊时期,在一个过分崇拜私有化、市场化、金钱化的竞争社会,群体不过是沙化个体的临时相加和局部聚合。换句话说,
”、“消费群体”、“劳力资源”、“利益关联圈”等概念取代。除了战争或灾害等特殊时期,在一个过分崇拜私有化、市场化、金钱化的竞争社会,群体不过是沙化个体的临时相加和局部聚合。换句话说, 民已经开始解体。特别是对于
民已经开始解体。特别是对于 文工作者来说,这些越来越丧失群体
文工作者来说,这些越来越丧失群体 感、共同目标、利益共享机制的
感、共同目标、利益共享机制的 民也大大变质,迥异于启蒙和革命小说里的形象,比方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形象。你不得不承认:在眼下,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比理
民也大大变质,迥异于启蒙和革命小说里的形象,比方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形象。你不得不承认:在眼下,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比理 外
外 更火
更火 。地摊上的色
。地摊上的色 和
和 力比经典作品更畅销。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不知是大众文化给大众洗了脑,还是大众使大众文化失了身,用遥控器一路按下去,很少有几个电视台不在油腔滑调、胡言
力比经典作品更畅销。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不知是大众文化给大众洗了脑,还是大众使大众文化失了身,用遥控器一路按下去,很少有几个电视台不在油腔滑调、胡言 语、拜金纵欲、附势趋炎,靠文化露
语、拜金纵欲、附势趋炎,靠文化露 癖打天下。在所谓
癖打天下。在所谓 民付出的
民付出的 民币面前,在收视率、票房额、排行榜、
民币面前,在收视率、票房额、排行榜、 气指数的压力之下,文化的总体品质一步步下行,正在与“芙蓉姐姐”(中国)或“脱衣大赛”(
气指数的压力之下,文化的总体品质一步步下行,正在与“芙蓉姐姐”(中国)或“脱衣大赛”( 本)拉近距离。身逢此时,一个心理脆弱的文化
本)拉近距离。身逢此时,一个心理脆弱的文化 英,夹着两本哲学或艺术史,看到贫民区里太多挺着大肚腩、说着粗痞话、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八卦新闻、随时可能犯罪和吸毒的冷漠男
英,夹着两本哲学或艺术史,看到贫民区里太多挺着大肚腩、说着粗痞话、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八卦新闻、随时可能犯罪和吸毒的冷漠男 ,联想到苏格拉底是再自然不过的:如果赋予民众司法权,一阵广场上的吆喝之下,哲
,联想到苏格拉底是再自然不过的:如果赋予民众司法权,一阵广场上的吆喝之下,哲 们都会小命不保吧?
们都会小命不保吧?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上帝死了,是一个现代的事件。
 民死了,是一个后现代的事件。
民死了,是一个后现代的事件。
至少对很多 来说是这样。
来说是这样。
上帝退场以后仍然不乏道德支撑。比如有一种低阶道德,即以私利为出发点的道德布局,意在维持公共生活的安全运转,使无家可归的心灵暂得栖居。商 们和长官们不是愤青,不会永远把“自我”或者“叛逆”当饭吃。相反,他们必须
们和长官们不是愤青,不会永远把“自我”或者“叛逆”当饭吃。相反,他们必须 际和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能没有社会视野和声誉意识,因此会把公共关系做得十分温馨,把合作共赢讲得十分动
际和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能没有社会视野和声誉意识,因此会把公共关系做得十分温馨,把合作共赢讲得十分动 ,甚至在环保、慈善等方面一掷千金,成为频频出镜的
,甚至在环保、慈善等方面一掷千金,成为频频出镜的 心模范,不时在
心模范,不时在 色小散文或烫金大宝典那里想象自己的
色小散文或烫金大宝典那里想象自己的 格增高术——可见道德还是
格增高术——可见道德还是 见
见
 的可心之物。应运而生的大众文化明星或民间婆巫汉,也会热
的可心之物。应运而生的大众文化明星或民间婆巫汉,也会热 推出“心灵
推出“心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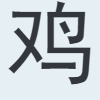 汤(包括心灵野
汤(包括心灵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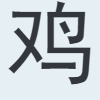 汤)”,炖上四书五经或雷
汤)”,炖上四书五经或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