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大觉。这一觉睡得可真够长的。可帝国的士兵,在战场上,却要以血 之躯抵抗凌厉的弹丸。这本身就是一场不平等的对弈。唉,圆明园不失火的话,昏睡百年的大清王朝,恐怕还不会醒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把火又该烧#轰然烧得疼了点,但不疼,则无法惊醒。
之躯抵抗凌厉的弹丸。这本身就是一场不平等的对弈。唉,圆明园不失火的话,昏睡百年的大清王朝,恐怕还不会醒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把火又该烧#轰然烧得疼了点,但不疼,则无法惊醒。
纵火的强盗固然可恶,但失职(或渎职)的守护者,同样可恨。一个麻木的民族,终于被坚船利炮 进了死胡同,再也没有退路,除了背水一战之外,似乎还应反思,检讨失败的原因。张宏杰在《回首
进了死胡同,再也没有退路,除了背水一战之外,似乎还应反思,检讨失败的原因。张宏杰在《回首 新觉罗们》一文中说得好:“
新觉罗们》一文中说得好:“ 们大概都以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应该算在乾隆的孙子道光帝
们大概都以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应该算在乾隆的孙子道光帝 上,子孙的无能不应抹杀祖先的伟大,可是也许很少有
上,子孙的无能不应抹杀祖先的伟大,可是也许很少有 知道,乾隆皇帝和鸦片战争也有那么一点意味
知道,乾隆皇帝和鸦片战争也有那么一点意味 长的关系。”鸦片战争原始的种子,在乾隆的脚下开始埋下了。乾隆在圆明园里盖西洋楼,仅仅实现了中西建筑文化的媾和(况且还是不伦不类的),但这两大文明,却呈现为格格不
长的关系。”鸦片战争原始的种子,在乾隆的脚下开始埋下了。乾隆在圆明园里盖西洋楼,仅仅实现了中西建筑文化的媾和(况且还是不伦不类的),但这两大文明,却呈现为格格不 的局面,终将产生悲剧
的局面,终将产生悲剧 的冲突。所谓的鸦片,仅仅是一根导火索。但这足以使圆明园像火药桶一样
的冲突。所谓的鸦片,仅仅是一根导火索。但这足以使圆明园像火药桶一样
 了。我把那带有烟熏痕迹的残砖碎瓦,视为冷却的弹片。
了。我把那带有烟熏痕迹的残砖碎瓦,视为冷却的弹片。
许多 都凭印象以为圆明园是一座“全盘西化”的皇家园林,而大水法、方外观、海晏堂等西洋景代表着其灵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圆明三园占地52oo亩以上,殿堂庙宇、亭台楼阁、桥梁轩榭、馆院廊庑等各类园林建筑加起来,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超了紫禁城的全部建筑面积)。而整个西洋楼建筑群位于长春园一隅,占地1oo余亩,只相当于圆明园全局的五十分之一。有
都凭印象以为圆明园是一座“全盘西化”的皇家园林,而大水法、方外观、海晏堂等西洋景代表着其灵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圆明三园占地52oo亩以上,殿堂庙宇、亭台楼阁、桥梁轩榭、馆院廊庑等各类园林建筑加起来,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超了紫禁城的全部建筑面积)。而整个西洋楼建筑群位于长春园一隅,占地1oo余亩,只相当于圆明园全局的五十分之一。有 说这不过是“乾隆皇帝的一时心血来
说这不过是“乾隆皇帝的一时心血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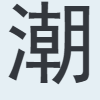 之作”,纯属点缀
之作”,纯属点缀 的小品。可见中国的帝王并不见得真住得惯洋房,亦非为了追求中西合璧,仅仅是在炫耀自家园地包罗万象、百花齐放。
的小品。可见中国的帝王并不见得真住得惯洋房,亦非为了追求中西合璧,仅仅是在炫耀自家园地包罗万象、百花齐放。
然而在火灾中,以石料砌筑的西洋楼,比“土木工程”的中式建筑稍占点“便宜”,被烈焰吞噬之后,至少还能多剩下点“骨 ”呀什么的,以证明那“最后的晚餐”。以至迟到的观众,面对着剩菜残羹,误认为圆明园原本就是一席“西式套餐”呢。并且,似乎还不够原汁原味……所以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法国留学生,觉得圆明园被毁固然可惜,但充斥于其中的,原本就是模仿痕迹浓重的“赝品”,并不值得为之痛心疾首。
”呀什么的,以证明那“最后的晚餐”。以至迟到的观众,面对着剩菜残羹,误认为圆明园原本就是一席“西式套餐”呢。并且,似乎还不够原汁原味……所以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法国留学生,觉得圆明园被毁固然可惜,但充斥于其中的,原本就是模仿痕迹浓重的“赝品”,并不值得为之痛心疾首。
这种普遍存在的错觉,是应该及时纠正的。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oo2年11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重现”圆明园》的重 稿件:“1o月18
稿件:“1o月18 是一个比‘9.11’更值得悼念的
是一个比‘9.11’更值得悼念的 子。142年前的今天,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过一场
子。142年前的今天,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过一场 类文明的大劫难——火烧圆明园。这座中国清代康乾盛世修造的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无论其艺术价值还是历史地位,都是美国纽约世贸大楼无法比拟的。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尽劫难的圆明园已被悲怆与荒凉掩盖,并逐渐从
类文明的大劫难——火烧圆明园。这座中国清代康乾盛世修造的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无论其艺术价值还是历史地位,都是美国纽约世贸大楼无法比拟的。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尽劫难的圆明园已被悲怆与荒凉掩盖,并逐渐从 们的记忆中消失,年轻一代甚至根本想象不出她的旷世盛景,以致将圆明园中的一个景点——西洋楼与整个圆明园划等号。”成语盲
们的记忆中消失,年轻一代甚至根本想象不出她的旷世盛景,以致将圆明园中的一个景点——西洋楼与整个圆明园划等号。”成语盲 摸象,形容的正是这种谬误:摸到
摸象,形容的正是这种谬误:摸到 或脚或尾
或脚或尾 ,就以为是大象的形状。摸到西洋楼,就以为是圆明园的核心或全部。
,就以为是大象的形状。摸到西洋楼,就以为是圆明园的核心或全部。
或许不能完全怪不知 的游客。空空
的游客。空空
 的圆明园,除了西洋楼遗墟,似乎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摸了。
的圆明园,除了西洋楼遗墟,似乎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摸了。
难道,我还能摸到更多的东西吗?
除非换一种方式。转而抚摸历史,抚摸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的海市蜃楼。
我的手 ,就有乾隆年间宫廷画家沈源、唐岱实地写生的绢本彩色《圆明园四十景图》——当然是复印件,原作至今仍为
,就有乾隆年间宫廷画家沈源、唐岱实地写生的绢本彩色《圆明园四十景图》——当然是复印件,原作至今仍为 黎国家图书馆占有。我在纸上摸来摸去,捕捉到圆明园真正的灵魂。我摸到了山,摸到了水(譬如福海),摸到了九孔桥,摸到了大宫门……甚至还差点摸到了乾隆的龙袍,和香妃的裙裾。
黎国家图书馆占有。我在纸上摸来摸去,捕捉到圆明园真正的灵魂。我摸到了山,摸到了水(譬如福海),摸到了九孔桥,摸到了大宫门……甚至还差点摸到了乾隆的龙袍,和香妃的裙裾。
我摸到了“西湖”。还纳闷呢:西湖不是在杭州吗?原来福海“抄袭”了西湖。诸多水景,都与西湖的风景点同名:三潭印月、南屏晚钟、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柳 闻莺……杭州有西施。好在北京也有香妃。都是大美
闻莺……杭州有西施。好在北京也有香妃。都是大美 。
。
圆明园的西洋楼里,有海伦吗?拿那2o幅西洋楼铜版画(同样为 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与绢本《圆明园四十景画》一比,方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西洋楼是用14年时间修竣的。而整个圆明园却苦心经营了15o多年,不断地锦上添花,增筑新景。这所谓的四十景,皆是元老,集中国古典建筑之大成,都曾经乾隆逐一赐名并点评,堪称国色天香。兹录如下:正大光明、勤政亲贤、
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与绢本《圆明园四十景画》一比,方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西洋楼是用14年时间修竣的。而整个圆明园却苦心经营了15o多年,不断地锦上添花,增筑新景。这所谓的四十景,皆是元老,集中国古典建筑之大成,都曾经乾隆逐一赐名并点评,堪称国色天香。兹录如下:正大光明、勤政亲贤、 天
天 处、长春仙馆、茹古涵今、九洲清宴、镂月开云、山高水长、坦坦
处、长春仙馆、茹古涵今、九洲清宴、镂月开云、山高水长、坦坦
 、天然图画、万方安和、杏花春馆、上下天光、慈云普护、碧桐书院、曲院风荷、澡身浴德、夹镜鸣琴、别有
、天然图画、万方安和、杏花春馆、上下天光、慈云普护、碧桐书院、曲院风荷、澡身浴德、夹镜鸣琴、别有 天、接秀山房、蓬岛瑶台、涵虚朗鉴、平湖秋月、方壶胜境、四宜书屋、廓然大公、西峰秀色、鱼跃莺飞、北远山村、坐石临流、澹泊宁静、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武陵春色、月地云居、
天、接秀山房、蓬岛瑶台、涵虚朗鉴、平湖秋月、方壶胜境、四宜书屋、廓然大公、西峰秀色、鱼跃莺飞、北远山村、坐石临流、澹泊宁静、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武陵春色、月地云居、 天琳宇、鸿慈永祜、汇芳书院、多稼如云、濂溪乐处。风流皇帝乾隆的
天琳宇、鸿慈永祜、汇芳书院、多稼如云、濂溪乐处。风流皇帝乾隆的
 ,全投映在他为这四十大景所起的名字里了。何其骄傲,何其虚荣,何其潇洒。
,全投映在他为这四十大景所起的名字里了。何其骄傲,何其虚荣,何其潇洒。
除“御批”的四十景外,圆明三园可圈可点的中式古典建筑还有许多:长春园的玉玲珑馆、长春桥、澹怀堂、思永斋、法慧寺、花庙、绮春园的含辉楼、绿满轩、招凉榭、迎晖殿、庄严法界、点景房、春泽斋、涵秋馆、凤麟洲、鉴碧亭、生冬室……
尤其值得提及的,有位于长春园西湖小岛( 造)的海岳开襟,不仅名字起得很有气势,而且高阁凌云,周围有配殿、方亭、圆廊及牌坊环绕;火烧圆明园时,此建筑因坐落于水中央而幸存,但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在4o年后,还是被八国联军的铁蹄摧毁。在长春园中心岛上,含经堂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淳化轩是圆明园内最大建筑——乾隆仿照紫禁城宁寿宫,为自己营造了太上皇宫殿,供“退休”后使用;他真是一位会享清福的“离休老
造)的海岳开襟,不仅名字起得很有气势,而且高阁凌云,周围有配殿、方亭、圆廊及牌坊环绕;火烧圆明园时,此建筑因坐落于水中央而幸存,但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在4o年后,还是被八国联军的铁蹄摧毁。在长春园中心岛上,含经堂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淳化轩是圆明园内最大建筑——乾隆仿照紫禁城宁寿宫,为自己营造了太上皇宫殿,供“退休”后使用;他真是一位会享清福的“离休老 部”。另外,在与西洋楼景区螺狮牌楼唇齿相依处,有带水门的狮子林,系乾隆根据苏州名园狮子林而照葫芦画瓢的;在荷花池里泛龙舟,他一定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回到江南了……看来乾隆造景,不仅有西洋建筑之“赝品”,还
部”。另外,在与西洋楼景区螺狮牌楼唇齿相依处,有带水门的狮子林,系乾隆根据苏州名园狮子林而照葫芦画瓢的;在荷花池里泛龙舟,他一定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回到江南了……看来乾隆造景,不仅有西洋建筑之“赝品”,还 模仿南方水乡的风韵。难怪有专家说圆明园“将古今、南北、中西建筑之类和谐地集于一身”呢。御用文
模仿南方水乡的风韵。难怪有专家说圆明园“将古今、南北、中西建筑之类和谐地集于一身”呢。御用文 曾咏诗:“
曾咏诗:“ 间天上诸景备,移天缩地
间天上诸景备,移天缩地 君怀。”圆明园浓缩了古今中外建筑艺术之
君怀。”圆明园浓缩了古今中外建筑艺术之 髓,相当于一座海纳百川的露天博物馆。恐怕只有康熙、乾隆这样的盛世之君(大手笔),才有泼墨谱写这史诗长卷的信心与实力。毕竟,康乾盛世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大清的皇帝自然堪称“全球首富”,花点钱投资房地产——算什么?小菜一碟!
髓,相当于一座海纳百川的露天博物馆。恐怕只有康熙、乾隆这样的盛世之君(大手笔),才有泼墨谱写这史诗长卷的信心与实力。毕竟,康乾盛世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大清的皇帝自然堪称“全球首富”,花点钱投资房地产——算什么?小菜一碟!
正是从乾隆晚期,中国这只曾经遥遥领先的兔子,见没 能赶得上自己,开始睡懒觉了。而欧洲诸国,则通过产业革命而获得了加速度,奋起直追。在东西方文明的“
能赶得上自己,开始睡懒觉了。而欧洲诸国,则通过产业革命而获得了加速度,奋起直追。在东西方文明的“ 兔赛跑”中,名次将从此颠倒。西
兔赛跑”中,名次将从此颠倒。西 迈着稳健的步伐,超越昏睡百年的中国而打
迈着稳健的步伐,超越昏睡百年的中国而打 新的纪录。两者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等到中国
新的纪录。两者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等到中国 快成为亡国
快成为亡国 了,才如梦方醒。
了,才如梦方醒。
从康熙到雍正,直至乾隆,大清帝国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恰恰印证了一句俗话:富不过三代。“满洲 世代相传的进取心在乾隆这一代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像汹涌的
世代相传的进取心在乾隆这一代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像汹涌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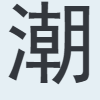 水一样,达到顶点之后,开始逐渐消退了。因为前面不再有什么可激起他们竞争欲望的东西。自命不凡的乾隆,现在全部身心沉浸在自我欣赏的快感当中了……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他
水一样,达到顶点之后,开始逐渐消退了。因为前面不再有什么可激起他们竞争欲望的东西。自命不凡的乾隆,现在全部身心沉浸在自我欣赏的快感当中了……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