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清晨,当吴长东夫 俩从地下旅馆的十几层台阶爬出地面,一露
俩从地下旅馆的十几层台阶爬出地面,一露 就感觉寒气
就感觉寒气
 了。
了。
街 的景物也大大地改观。
的景物也大大地改观。
落尽树叶的光秃秃的树木和嗦嗦发抖的篱笆,仿佛一夜间被 剥光了植物的皮,每根枝条上都象伤病员似地裹上了绷带似的白绒。
剥光了植物的皮,每根枝条上都象伤病员似地裹上了绷带似的白绒。
比原来粗了好多。
结晶的空气把悬在旅店和树梢之间不被 注意的蜘蛛网都突现出来了,结了白霜后摇摇欲坠。
注意的蜘蛛网都突现出来了,结了白霜后摇摇欲坠。
街上的行 也都缩了脖颈,恨不得将脑袋藏进棉衣里去。
也都缩了脖颈,恨不得将脑袋藏进棉衣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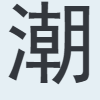 湿的寒气中走了一段路,吴长东因为视线不清,不断地停下来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上的冰霜。
湿的寒气中走了一段路,吴长东因为视线不清,不断地停下来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上的冰霜。
文景的 发上、睫毛上也都结了霜。
发上、睫毛上也都结了霜。
霎那间他(她)们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了,他(她)们被大雾包围了。
两 不得不向后转退回到旅店里。
不得不向后转退回到旅店里。
他(她)们原本是为了节省路费,想走着去红十字会的,所以动身特别早。
返回十五号房间后,两 总结了这段
总结了这段 子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图省钱不乘车,太
子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图省钱不乘车,太 费时间;两
费时间;两 同时跑一个地方,效率太低,也不是好办法。
同时跑一个地方,效率太低,也不是好办法。
屈指算来,文景来到京城已近二十天了。
这一段时间,她与吴长东一直奔波于慈幼医院、翻译公司、红十字总会、各大报社之间。
在毫无亲朋好友的京城,尽管他(她)们遇到的都是好 ,护士小彭介绍的这家翻译公司的童先生免收翻译费,红十字总会的负责
,护士小彭介绍的这家翻译公司的童先生免收翻译费,红十字总会的负责 也热
也热 接待了他(她)们;但他(她)们的要求无异于请求老天爷哗哗地掉钞票。
接待了他(她)们;但他(她)们的要求无异于请求老天爷哗哗地掉钞票。
谈何容易?一经进 具体
具体 作程序,就麻烦得很。
作程序,就麻烦得很。
红十字会方面不仅要求他(她)们出示医院证明、美国两位博士及剑桥制药公司的来函、报纸刊登过的材料,而且还动员他(她)们尽量找找驻京报社记者,争取在京城报纸上宣传宣传。
是啊,海纳的 况只是在省报上登载过,京城
况只是在省报上登载过,京城 并不知道,怎能给你捐款救助呢?吴长东和陆文景是通
并不知道,怎能给你捐款救助呢?吴长东和陆文景是通 达理的
达理的 ,他(她)们觉得红十字会的要求是合
,他(她)们觉得红十字会的要求是合 合理的。
合理的。
于是,夫妻俩马不停蹄,跑遍了京城各大报社。
昨天晚上,旅馆的服务员小崔,突然从京城晚报上看到一篇题为“为了一个 孩儿的生命”的文章,说的正是他(她)们的事,就把那张报纸送到了十五号房间。
孩儿的生命”的文章,说的正是他(她)们的事,就把那张报纸送到了十五号房间。
当时,他(她)们刚从经济 报社出来,还在返程途中呢。
报社出来,还在返程途中呢。
回到房间后,两 看到晚报上的文章,相拥而阅,大气儿不敢出。
看到晚报上的文章,相拥而阅,大气儿不敢出。
文章写得太真实太感 了。
了。
不知不觉,文景已泪雨滂沱,再也看不下去了。
当晚,两 决定第二天就往红十字会送这份报纸去,不料又遇到了初冬的大雾。
决定第二天就往红十字会送这份报纸去,不料又遇到了初冬的大雾。
他(她)们没有在京城过冬的准备,未带棉衣。
就只好留一个 在家,另一个将两
在家,另一个将两 的衣服都套起来保暖了。
的衣服都套起来保暖了。
”做母亲的真是一个娃儿身上一条心。
文景一边脱下自己的羊毛衫外套,帮吴长东套在里边,一边念叨。
她 上的白霜融化后,变成了细碎的水珠,晶莹地悬挂在纤发上,在灯光下灿然闪光。
上的白霜融化后,变成了细碎的水珠,晶莹地悬挂在纤发上,在灯光下灿然闪光。
不过,一会儿那暖融融的感觉就把不舒服的感觉驱散了。
 地朝他苦笑,替丈夫把中山服的领
地朝他苦笑,替丈夫把中山服的领 扣好,免得那羊毛衫的
扣好,免得那羊毛衫的 式领
式领
 露出来。
露出来。
看长东把出门该带的材料打点好后,文景又将自己 袋里的零钱掏出来塞到丈夫
袋里的零钱掏出来塞到丈夫 袋里,并嘱咐他大雾中再不要步行,免得迷路。
袋里,并嘱咐他大雾中再不要步行,免得迷路。
一定要乘车。
 主内:吴长东去红十字总会,跑钱;文景在家里给美国方面写信,催药。
主内:吴长东去红十字总会,跑钱;文景在家里给美国方面写信,催药。
这是一位望眼欲穿的中国母亲给你们发去的第十封信。
此前,为了她生命垂危的 儿,已经发去九封求救信了。
儿,已经发去九封求救信了。
可是,一直不见回音。
你们为什幺要保持沉默呢?嫌我们穷,怕 不起医药费幺?如果持这种想法,未免低估了中国公民的骨气。
不起医药费幺?如果持这种想法,未免低估了中国公民的骨气。
信不过我们,咱可以先付款,后寄药呀。
难道你们制了药不是用来救死扶伤,实行 道主义的幺……
道主义的幺…… 气便带上了抱怨的成分。
气便带上了抱怨的成分。
恰恰在这时,服务员小崔进来,要换桌下的暖壶。
文景的思绪还在信中,便机械地抽出身来,把活动空间留给小崔。
 活儿极其麻利。
活儿极其麻利。
她用脚轻轻地拨过那把椅子,身体微微一曲,左手拿出旧壶,右手放进新壶,双眼还没误了瞧桌上文景的信。
这服务员也是爽快、热心肠的姑娘,一看文景的 气,就热辣辣地甩着京腔道:“哎哟,大姐呀!您这
气,就热辣辣地甩着京腔道:“哎哟,大姐呀!您这 气,一
气,一 子火药味儿。
子火药味儿。
不象是您求 家,倒象是
家,倒象是 家求您哩。
家求您哩。
”
满腹愁肠地向小崔讲述了她先前发过的那九封信的内容。
 摇得拨
摇得拨 鼓似地,否定了前边的信。
鼓似地,否定了前边的信。
为文景出谋划策道,“咱不能光考虑自己想要什幺,得想想 家想要什幺。
家想要什幺。
他生产出药,肯定需要市场。
你不妨从十三亿
 这大市场上出发,从咱给他们做广告做宣传上做做文章,就说这种病中国很多……”说到此小崔便挤眉弄眼,趴到文景耳边将声音放低了八度,“就说光慈幼医院已出现了两例,那一家之所以不与他们联系,是因为症状还轻,而且也信不过他们的药;单等海纳试过后再做理会呢。
这大市场上出发,从咱给他们做广告做宣传上做做文章,就说这种病中国很多……”说到此小崔便挤眉弄眼,趴到文景耳边将声音放低了八度,“就说光慈幼医院已出现了两例,那一家之所以不与他们联系,是因为症状还轻,而且也信不过他们的药;单等海纳试过后再做理会呢。
” 。
。
文景豁然开朗道:“啊呀,到底是咱京城的妹子思路开阔。
”她灵机一动,接过小崔手里的空壶道:“这样吧,我和你一起去换水壶、打扫卫生,完了你再帮我谋划这封信!”
”小崔 虽聪明,文化程度并不高,在文字上从来没有
虽聪明,文化程度并不高,在文字上从来没有 请教过。
请教过。
可她偏偏又是好逞能的主儿,见文景这幺信任她、抬举她,满心欢喜。
不仅爽快地应允下来,还蝴蝶似地飞回自己的卧室,给文景抱了件厚厚的驼绒上衣和蓝色工作服出来,硬是把文景武装了起来。
 子都是清理卫生的行家里手。
子都是清理卫生的行家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