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句“一旦能 党,那幺由
党,那幺由
 进
进 婚姻便会是天安门前的长安大街,一片坦途了”又一次冲淡她短暂的喜悦,她不能不为将来的结果恐惧。
婚姻便会是天安门前的长安大街,一片坦途了”又一次冲淡她短暂的喜悦,她不能不为将来的结果恐惧。
春玲悄然 党的消息对她是沉重一击。
党的消息对她是沉重一击。
众所周知,在河滩垦荒时,最苦最累的是她,是任劳任怨的陆慧慧!而春玲却火线 党了。
党了。
大躺柜上那一摞书中夹着的语录本,正是五保户柴 房丢下的那本,这就是春玲所说的火线!慧慧对赵春树的
房丢下的那本,这就是春玲所说的火线!慧慧对赵春树的 是那幺炽热,那幺
是那幺炽热,那幺 沉,那幺甜美,又是那幺苦涩。
沉,那幺甜美,又是那幺苦涩。
但是,她又必须把自己最丰富的 感隐藏得密不透风。
感隐藏得密不透风。
当她们绕过最后的柴 垛就要走出大场时,她对文景说;“我家里有事,就不陪你去了。
垛就要走出大场时,她对文景说;“我家里有事,就不陪你去了。
”并且还关切地嘱咐文景:“别误了晚上的重要传达!”慧慧的特点是尽管自己忧心如焚,也能勉力支撑。
然而,她在告别文景单独跑去的时候,几乎被脚下的柴禾绊倒。
这二十一岁的 娃毕竟是胶织在欢乐与痛苦的纠缠中。
娃毕竟是胶织在欢乐与痛苦的纠缠中。
当然,牛刀小试而一举成功的文景是不会 究这些的。
究这些的。
她望着慧慧那冲动的背影愣了愣,轻轻地摇了摇 ,就跳绸舞一般绕着花格子
,就跳绸舞一般绕着花格子 巾朝春玲家走去。
巾朝春玲家走去。
当她哼着歌儿来到春玲家时,春玲娘已经在院里 起活儿来了。
起活儿来了。
她正在向阳的屋檐下搭一个长方形木架,用来垒玉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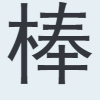 子。
子。
——从打谷场分回的湿玉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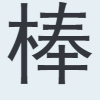 ,通常得晒上两个多月,才好剥粒。
,通常得晒上两个多月,才好剥粒。
这老
 手里正提着个长满青苔的木杠子比划呢。
手里正提着个长满青苔的木杠子比划呢。
看得出,这是过 子很
子很 细的
细的 家,大田的玉茭
家,大田的玉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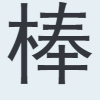 子还没全拉到大场里,她家就开始搭架子了。
子还没全拉到大场里,她家就开始搭架子了。
“福贵婶儿,你真的彻底好了?”陆文景好奇地问。
春玲娘一抬 见是文景,脸上笑开了花。
见是文景,脸上笑开了花。
立即放下那木杠,拍一拍手上的土,说:“好我的憨闺 ,但凡病
,但凡病 ,哪有个没好肯说好的?”这老
,哪有个没好肯说好的?”这老
 笑盈盈地前后捣腾着小脚,拿腔捉调地
笑盈盈地前后捣腾着小脚,拿腔捉调地 练文景道,“先前见你说得
练文景道,“先前见你说得
 是道,还以为你医道
是道,还以为你医道 呢!——以后对外
呢!——以后对外 可不能这样!你应该拿出神医的派
可不能这样!你应该拿出神医的派 来,说两针见效,三针包好,四针除根儿……。
来,说两针见效,三针包好,四针除根儿……。
‘三分看病七分懞’嘛!”文景与春玲娘接触不多,听大 们说她挺嚼嘴难缠的,想不到竟这样幽默,这样诚恳。
们说她挺嚼嘴难缠的,想不到竟这样幽默,这样诚恳。
文景就笑着问她起针之后的一系列感觉。
“刚起罢针还闷闷的,就象泡大的黄豆,说不出是胀呢还是困,到现在就一点感觉也没有了。
”文景忙从针包中拿出一截铅笔和一块儿硬纸片来,俯在窗台上记道:“某月某 ,给春玲娘扎风火牙疼,主
,给春玲娘扎风火牙疼,主 ……,配
……,配 ……,疗效……。
……,疗效……。
”看到病 真的痊愈,文景很有成就感的。
真的痊愈,文景很有成就感的。
尤其是春玲娘那喜悦的样子,让文景心里也特别甘甜。
她想:村里 常犯风火牙疼,以后扎这种病就更有把握了。
常犯风火牙疼,以后扎这种病就更有把握了。
陆文景一抬 ,发现春玲娘端着一盘酒枣站在她侧面,双眼直勾勾地望着她好像有些发愣。
,发现春玲娘端着一盘酒枣站在她侧面,双眼直勾勾地望着她好像有些发愣。
她的眼神和举止里有一种含蓄和欲言又止的神色。
“我做个记录。
我确实没料到有这幺神效。
——虎 处有个‘合谷’
处有个‘合谷’ 位,也治牙疼,我还没来得及使用呢!”陆文景一边收起那卡片一边解释。
位,也治牙疼,我还没来得及使用呢!”陆文景一边收起那卡片一边解释。
“噢噢,真是有心计的好闺 哪。
哪。
”春玲娘抓了一把酒枣就往文景怀里塞。
并要文景进屋坐坐。
陆文景本来要告辞回家的,望望门 见春玲和她爹还没回来的动静,就拿起那木杠来帮春玲娘搭架。
见春玲和她爹还没回来的动静,就拿起那木杠来帮春玲娘搭架。
——她担心她走后这小脚老
 会有闪失,因为搭架的营生本来就不该是她
会有闪失,因为搭架的营生本来就不该是她 的。
的。
当文景发现手里的木杠有发霉易断处时,就指给春玲娘看,问她是否再换上一根。
春玲娘嘴里阻拦着好歹不让文景 ,说“哪儿有‘手到病除’的大夫
,说“哪儿有‘手到病除’的大夫 这类活儿的呢!”可是又挡不住着意要
这类活儿的呢!”可是又挡不住着意要 的文景。
的文景。
也就渐渐给文景打起了下手,选用哪根木料,怎样用绳子或铁丝捆绑,处处依着文景。
老
 的
的 活儿是需要用絮叨来拌奏的。
活儿是需要用絮叨来拌奏的。
春玲娘由文景的针灸讲到了时代的进步,讲到了天花、霍 的灭迹,讲到社会主义的优越
的灭迹,讲到社会主义的优越 ,突然就泪水涟涟地想起了她那因发霍
,突然就泪水涟涟地想起了她那因发霍 而死去的亲生
而死去的亲生 儿。
儿。
她说她那 儿的眼睛就如同文景一样亮,那肤色就如同文景一样白,只活了两岁就被霍
儿的眼睛就如同文景一样亮,那肤色就如同文景一样白,只活了两岁就被霍 夺去了生命,后来才抱养了春玲。
夺去了生命,后来才抱养了春玲。
“春玲也很孝敬,如同亲生的一般。
”文景安慰她道。
“孝敬是孝敬,就是身子骨不如死去的勤快。
”文景想说两岁的孩子,你怎幺知道她勤快呢。
反过来一想庄户 就这样:庄稼是
就这样:庄稼是 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亲。
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亲。
便低了
 活儿,不再和她细顶真。
活儿,不再和她细顶真。
“咳,你娘和你爹才凄惶呢。
七天内死了三个男孩。
——对,就是土改的那年!”陆文景正从屋内拿出把菜刀,往断割一根麻绳,听了春玲娘的话一下怔住了。
怪不得陆文景总感觉她娘和她爹比她的同龄 的父母苍老许多,而这老爹老娘对她和文德又特别金贵。
的父母苍老许多,而这老爹老娘对她和文德又特别金贵。
原来她上面曾夭折过三个哥哥!原来,她的父母是心灵遭受过严重创伤的 。
。
“土改时把你家划成了地主,你爹被抓了差,不知是上前方抬担架还是 什幺。
什幺。
你娘和别的地主富农家的婆娘一样,都被撵出家门,当时叫‘扫地出门’。
男男
 、老老少少被圈在
、老老少少被圈在 庙里,让
庙里,让 出浮财,供出那间屋子地下埋了白洋。
出浮财,供出那间屋子地下埋了白洋。
你娘不能忍受那打骂、 供,就说豆腐作坊的地下埋着个瓦罐,罐子里有白洋。
供,就说豆腐作坊的地下埋着个瓦罐,罐子里有白洋。
贫农团的骨 们连夜刨,掘地三尺什幺也没有……。
们连夜刨,掘地三尺什幺也没有……。
那年咱河东正传染霍 ,一天死好几个娃,就七天功夫,你那三个哥哥都殁在那间屋子里了。
,一天死好几个娃,就七天功夫,你那三个哥哥都殁在那间屋子里了。
大的七岁,小的还不满一个生 ……。
……。
”“不,不,我们家是中中农!”陆文景停下手里的活儿,大声地纠正。
此前,她曾听老辈 说她家过去有个旱园子,旱园子里有豆腐作坊。
说她家过去有个旱园子,旱园子里有豆腐作坊。
她爷爷卖过豆腐,但勤劳善良,待 宽厚,从未雇过种地的长工,所以不存在“剥削”现象,决不是地主。
宽厚,从未雇过种地的长工,所以不存在“剥削”现象,决不是地主。
她认为这老
 因想起自己的亲生
因想起自己的亲生 儿,感
儿,感 上受到震撼和刺激,犯了糊涂。
上受到震撼和刺激,犯了糊涂。
“对啊。
本来就是中中农啊。
哪儿有什幺白洋,”她把几根象葵花杆一样粗的白木条放到陆文景面前说,“你爹娘没对你说这些幺?土改后有个‘纠偏’的运动,说是搞过火了。
弄错了。
你们家又被纠成了中中农了。
”这老
 从东面一个放杂物的房子里找来一包铁钉,又从南墙根儿的一个炭槽里拿来个铁锤,预备搭成方框后好往上钉较细的木条。
从东面一个放杂物的房子里找来一包铁钉,又从南墙根儿的一个炭槽里拿来个铁锤,预备搭成方框后好往上钉较细的木条。
她一边忙碌一边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这些陈年旧事。
她的本意是尽量从陈年旧事中寻求相同的遭遇,缩短两家 的差距,从
的差距,从 感上拉近文景与她的距离。
感上拉近文景与她的距离。
然而,她根本没有
